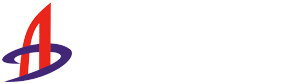實(shí)踐中,一些案件經(jīng)常出現證人所書(shū)寫(xiě)的書(shū)面材料,由證人對有關(guān)問(wèn)題進(jìn)行說(shuō)明,甚至以自書(shū)材料替代筆錄。有些辦案人員認為制作筆錄麻煩,偏好于收集自書(shū)材料。筆者認為,這種做法值得商榷。
制作筆錄是原則要求。監督執紀工作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一款、第四十條第一款分別賦予核查組、審查調查組對相關(guān)人員進(jìn)行談話(huà)、詢(xún)問(wèn)的權力,但未明確規定必須制作筆錄。監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賦予監委詢(xún)問(wèn)有關(guān)證人的權力,并要求“形成筆錄、報告等書(shū)面材料”。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紀律檢查機關(guān)案件檢查工作條例》第二十九條第(二)項規定,“收集證言,應對出證人提出要求,講明責任。證言材料要一人一證,可由證人書(shū)寫(xiě),也可由調查人員作筆錄,并經(jīng)本人認可。所有證言材料應注明證人身份、出證時(shí)間,并由證人簽字、蓋章或押印。”由此可見(jiàn),證人證言既可以形成筆錄,也可以由證人書(shū)寫(xiě)自書(shū)材料。但是,根據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紀律檢查機關(guān)案件檢查工作條例實(shí)施細則》第三十三條第3項規定,“調查人員與被調查人、證人、受侵害人談話(huà)時(shí),應制作《談話(huà)筆錄》”。筆者認為,監督執紀工作規則、監察法等未對證人證言的表現形式作出限制性規定,一是應對客觀(guān)實(shí)際的復雜性,未作出“必須制作筆錄”的限制性要求;二是基于辦案效率的考慮,不宜要求“必須制作筆錄”。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紀律檢查機關(guān)案件檢查工作條例》及其實(shí)施細則實(shí)施時(shí)間雖早于監督執紀工作規則和監察法,但基本精神是確保取證的規范和相關(guān)人員的權利保障。在實(shí)際操作中,制作筆錄更能反映事實(shí)的全貌和取證的合規、合法性,更利于確保證人身份的真實(shí)性以及對證人權利保障的落實(shí)。
制作筆錄是現實(shí)需要。對談話(huà)、詢(xún)問(wèn)過(guò)程形成筆錄,能夠完整反映身份核對、權利義務(wù)告知、事實(shí)細節的核對等要素。而自書(shū)材料僅是以證人記載的內容證明待證事實(shí),證據要素不全,效力與書(shū)證類(lèi)似,故實(shí)際操作中還需由辦案人員在自書(shū)材料上進(jìn)行接收備注。所以,在缺乏筆錄的情況下,審核自書(shū)材料,尚需對其是否系證人本人自書(shū)、證人的身份是否確定、表述是否系證人真實(shí)自愿做出等方面進(jìn)行審核。為彌補這種取證形式的不足,往往需要辦案人員對相關(guān)問(wèn)題進(jìn)行說(shuō)明,以確保自書(shū)材料的效力。筆者認為,只要具備制作筆錄的條件,一般應當制作筆錄,以免影響證據效力,進(jìn)而影響甚至否定待證事實(shí)。
制作筆錄可兼顧效率。一些辦案人員以工作繁忙、案情簡(jiǎn)單、條件有限等為由,怕麻煩、圖省事、求效率,偏好于讓證人自書(shū)材料。而實(shí)際上,這種“為了效率”的做法不僅沒(méi)有提高效率,還可能導致對證據來(lái)源及真實(shí)性的質(zhì)疑,甚至導致事實(shí)認定錯誤、處理或處分不當,給案件質(zhì)量埋下隱患,嚴重削弱執紀執法的嚴肅性和公信力。一旦出現一次失誤或者“推倒重來(lái)”,就會(huì )造成先期資源的浪費,更加大了后期彌補成本。
自書(shū)材料能補強筆錄。從證明力看,作為證人證言的自書(shū)材料是不能獨立存在的,但可以附屬于筆錄。在特殊情況下,如證人拒不接受詢(xún)問(wèn)而要求自書(shū)材料的,需要辦案人員將有關(guān)情況備注到該自書(shū)材料上或單獨作出書(shū)面說(shuō)明。以筆錄作支撐的自書(shū)材料,能夠彌補證人證言易變的先天不足,起到強化和加強筆錄效力的作用。因此,辦案人員可以要求證人自書(shū)材料,證人要求自書(shū)的,可以讓其自書(shū)。但原則上,無(wú)特殊情況下,應當制作筆錄,需要補強筆錄時(shí)可以使用自書(shū)材料。
綜上,筆者認為,證人證言的收集應以形成筆錄為主,以自書(shū)材料為輔,絕不能以自書(shū)材料代替筆錄。